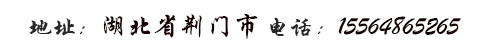北方案哈尔滨声音地图张立明
|
北方案记述北方地区的城市空间实践项目,介绍以北方视角解读并实践文化的团体及个人,并跟踪方案的实施情况。 有人这样评价张立明(Hitlike)的作品: “Hitlike似乎刻意保留了那些粗砺的东西在里面,形成了一种明确的风格。” 张立明老师本身似乎也是这样的,不做作,质朴而又有一种韧劲。 泽音文化与张立明老师初识是在一次名为“公共艺术:声音与地理实践”的艺术对谈,同为音乐类和城市实践类的项目,张立明老师的声音地图项目瞬间吸引了我们。因此,“北方案”工作组赶到了项目的发生地——冰城哈尔滨,走过松花江的冰面,踏过皑皑白雪,来采访他。 这大概是目前为止“北方案”记述的最北的(啊~也是项目开展地区气温最冷的)一个项目。在此得感谢张立明老师和碎冰社的刘禹老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带我们走了哈尔滨老道外和道里区域,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历史与现状。 北方案:为什么叫hitlike? 张立明:我99年来哈尔滨上大学,第一次上网,之前没上过网,我的高中是很封闭的,当时看到所有人在网上都起一个网名,我就想也给自己起一个网名。这个网名就是一个组合,HIT时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缩写,后边的单词就是一本词典扔在地下打开看到第一个单词,就是like。没什么特别的来历。后来他们说这个名字起的像希特勒似的。 北:为什么选择留在哈尔滨? 张:因为之前我没有想过要在哪工作,大学毕业之后其实是身不由己。因为我们那届是扩招生,在哈尔滨生活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的专业又是比较冷门的冶金专业,被迫找工作找到本溪去了,本溪工作了一年半,那个钢铁厂是文革时期劳改犯的场所,管理工人的模式是以管理劳改犯的方式,可想而知,他们的劳动强度很大,管理层对人的压榨很严重。所以那一年半的生活特别难过。之后,过年的时候回哈尔滨,借着聚会的机会,朋友就说“你别回去了”,就不想回去了,留在哈尔滨了。寄宿在碎冰社社长家里长达一个月。 北:为什么选择哈尔滨而不选择故乡呢? 张:因为老家的经济条件不行,我们这一辈的人,兄弟姐妹们都离开了,父母那一辈对我们的愿望就是,你离开这个地方了,那么你就成功了。老家已经走了很多人,没有几户在了。很多农村都是这样。 北:但是第一次做声音实践还是在自己家。 张:对,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暑假回家。那个时候其实是对声音最痴迷的时候,拿一个记者的采访机,很落后的那种单声道磁带机,录到什么声音都想马上重新再听一遍。回到老家就觉得,完全重新发现这个村庄了。原来没想过我的老家有这么多漂亮的东西,房前屋后,鸡犬相闻的那个动静儿,从小到大一直在听,但当用专门的一个设备再去听,就又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是对声音特别痴迷,也是对声音本体最痴迷。我当时就在想声音里的残缺,磁带机本身就是劣音质的,把声音很多东西实质上忽略掉了,频谱上少了很多东西,又把本身很复杂的声音变成了单声道。当时对残缺的事情特别特别感兴趣,对“缺失”这个事情感兴趣。那个时候是对声音最初的思考,04年,就快要毕业的时候。 北:怎么理解“残缺”这个概念呢? 张:那个声音已经从发声源彻底抽离出来了,与视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了。你不能再通过声音感知到原来的那个物,你明显感觉到那个物质缺失的过程。磁带机有一个功能,当它录一个人说话声的时候,你一说话的时候它转,你不说话的时候,当四周的分贝级降下来的时候,它停。我就利用这个功能记老母鸡下蛋的时候的“咯哒咯哒“叫的那个声音。录下来之后这个鸡的叫声会”哒哒哒哒哒……“的一直持续。这个东西本身是残缺的,中间缺了很多时间,但是又感觉比原来更完整。 北: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声音感兴趣?应该是从小时候就开始了吧? 张:我印象中最早的时候大概是六七岁的时候。农村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电子设备。我大伯父买了全村第一个收录机,收录一体的双卡的那种。那时候我是小孩子嘛,无所事事就跑他家去听。他当时就放了很多流行歌的磁带,他们都在园子里干活,我就在屋里翻盘放磁带,超享受那个动作,特别痴迷。那是第一次接触音乐、声音有关的东西。后来也是他家买了全村第一个电子琴,我就当这个东西是人生中最神秘的一个物件,天天去他家里想去玩这个。一直都特别遗憾没有一件自己的乐器,到初中我才有了一个竖笛。那个时候村里的孩子放假的时候都要到村里放羊、放牛,一般文学里边最浪漫的牧童骑黄牛的场景,其实是很枯燥的。牲畜到处乱跑啊,得追它,得撵它,你很少有时间能闲下来吹吹你的笛子。但也就是那段时间,我把我的笛子已经练的是炉火纯青了。到高中的时候我又改吹竹笛,就自己自学。 其实当时我对音乐,对笛子,已经按我的思路写出一个小册子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对中国的民族音乐特别感兴趣。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我自己的磁带机,以学外语为由,买了一个。买了大量的中国古曲的磁带,古筝啊,笛子啊,很难买到的,就那么几盘。晚上九点熄灯以后,黑暗中躺在床上听,听到十二点。到现在我也觉得,那个时间段里,我有我跟音乐最近的距离。整个三年里面,对我来说,我只有那几盒磁带。 北:那个时候对您来讲,音乐是不是已经可以作为表达方式出现了?它已经能表达你? 张:对。我小时候性格也很自闭,不太跟同学们说话,所以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听这个东西。我只是到毕业了参加工作了才逐渐跟人交谈,之前只有音乐。 北:那么声音地图是不是也是一个表达创作的结果? 张:对。你可以翻一下牛津字典里对音乐的定义:基于美的形式对声音的组织。可以说这是我对声音的组织。 北:是什么启发您有声音地图这个想法呢? 张:其实很早我就开始录制这些声音了,从04年夏季,一直到07年。而07年的时候,我当程序员了,工作得心应手之后会接一些私活儿,里边涉及到很多跟地图有关的东西,那时候已经有谷歌的电子地图,提供API,操作很方便。而国内实际上也开始有很多用地图做商业运行的这些操作。实际上我先看到了国外的做法,在欧洲已经有了这样的实践,但整个是我自己的技术摸索与实践。 北:比如您吹笛子的时候,会融合感情,是大家所熟知而理解的表达方式,而做声音地图呢,似乎是一个声音录制的集结,那您表达的这个点在哪里呢? 张:录音来讲,如果说是我个人感情的东西,是在录的时候的选择成分。比如秋风吹落叶落在地上,当时我可能想到某段音乐,或者某个人,我会个人化地录这个声音。而当你放在网络上呈现给普通的浏览者,他们未必就会有与我相同的感受。这也是声音一个复杂性,多元化的一面。但从整个声音的外缘化,整体性来看的话,首先是哈尔滨整个声音的一个地域性的留存。它偏向于一个地域化的某个阶段里声音的留存。很多声音再去原来的地方再也录不到了。 北:那对于您来说,哈尔滨的地域特征是什么? 张:相对而言,哈尔滨本身比国内大城市要落后很多,所以像老城区的声音是逐渐消失的,也是其他地方难以听到的。比如道外区靠近江边的地方,有个小楼房,楼上有放二人转、卡拉OK啊这种小歌厅,那时候放的那个音乐,那个飘飘渺渺的声音,这都是其他城市难以听到的。秋林服装地下的叫卖声,那个口音和现在也不一样了。他的意义对这个城市里的人更重要。如果我某天听到这个声音了,我会突然想到那几年,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的状态。 北:那有为这些声音特意去跑到一些地方去录制吗? 张:没有。曾经有朋友说大桥底下那个燕子的声音,推荐我去录。我产生过那个想法,但我没去录。因为那是他的经历。我声音地图里大部分的声音是走到哪就去录了。那个时候录音设备是不离手的,走到哪带到哪的。 北:声音地图上都是06、07年,那还会有一个更新吗? 张:不会了。对我来说就可以了,我和它能接触的时间就是这么长。我现在也没有动力去城市里面去录一些声音,可能我还有感兴趣的声音在,但不会再去做了。 北:那您还会继续做其他的声音项目吗? 张:我还在研究这方面的很多东西。包括今年想参与一个黑胶出版计划,出版声音的黑胶。我把我的录音选择拼接做了一个抽象的东西,我管它叫PureAbstractWork。这个计划目前搁浅中。相对的,我在寻找什么是具象的(Concrete)声音,我不认为我们平时所记录的声音是具象的。 北:具体是如何操作的呢? 张:这些就是我的实地录音,不同性质的,不同场合的,是我这么多年来录音里面的一个概括性的东西。我就倾向于表达这是我过去所有的录音,而这是抽象的东西。并想让它出现在黑胶上,非常实体的一张唱片里。 北:那您对黑胶有没有一种迷恋? 张:我倒是没有像黑胶迷那样。我买了黑胶是用来聆听的,我买的黑胶中一大半的音乐都是我音乐已经听烂过的,把黑胶买来放在那儿,实际上是对自己聆听时光的纪念吧。没有什么特别的,当然现在拿出来给别人听是另一种意义。我对音乐载体实质上是没有偏好的,比如说黑胶是最好的或是CD是最好的。因为我最早是听磁带听过来的,我知道磁带有它自己的魅力。你用磁带录声音回放的时候,除了声音还有磁带本身沙沙的背景声,很美妙。而黑胶实际上是有自己独特的杂音,有它材质本身的声音。 张:黑胶本身对我来说可能真的有它单独的魅力,比如说它的封面都很大。那个才叫唱片封面,可以做很多文章,设计的非常漂亮,跟CD那个小玩意儿不一样。黑胶真的是playmusic,你可以玩的,播放的时候更随心所欲,唱针放到什么位置,播放的时候你肉眼能看到。尤其你听电子舞曲的时候,舞曲节拍都看得到。 北:大家在利用音乐表达的时候,可能会选择弹奏,吹奏啊,作曲,电音混音啊这些,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些呢?那会不会以后来选择这些呢? 张:我是纯工作室派的。从小的性格决定了我不可能在公开的场合搞什么声音即兴啊。我不赞成即兴。即兴音乐本身确实是一个派别,但我觉得它已经过去了,最即兴的探索已经结束了,后来人只是拙劣地重复。它已经到了一个顶点,没有再往下走的可能,即兴对我来说没有意义。06、07年我出了几张小的CD,那个也是纯工作室里面出来的,用电脑来调变声音来重新组织的,是电子原音类的创作。你听他的声音,你听不出这个声音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已经把它调的完全变形了。 北:您最开始对声音地图的设想和最后做出来的有区别吗? 张:没有。因为本身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特别复杂的过程。 北:有些网站,他会在不同地域收集一些声音。 张:有个乡音网,几个老外做的。你会发现,都是外来者来做这样的事,本地人倾向于对本地的声音麻木。当我对哈尔滨变得麻木了以后,我就不太可能再对它进行记录了,很难了。因为我会觉得不再把它当成趣味。 北:有没有想过再换一个城市? 张:除非因为某些原因再去某些城市生活了,才可能会再记录。否则很难,比如坐火车去趟沈阳,只是为了去录几段声音,不太可能。 北:有没有想过一种模式调动各地一起来做? 张:之前已经有人想过了。比如说十几年前姚大钧的北京声音小组,记录北京胡同的声音现象,曾经在网上发布过一次北京声音档案,北京十几年前的声音。更早可能就只有学院派做田野考察,采风。 张:而且我没有那种一定要记录下这个地方特色的声音,对我来说,更多的记录是个人化的,有很多美学上的出发点在里面。比如说,我跟你说的蜂群。 北:对这些你喜欢的这个声音的截取点,你愿意怎么样去描述它? 张:多元微观的聚集。可以在一个小空间里同时成型。我不喜欢一个偶发的,单一的凸显出的声音。我不是很喜欢主题的那种(声音),因为主题已经被玩尽了。我最讨厌为了声音而去录制的,而应该是你生命里平行的事件,是你经历了这个事件而把它记录下来,而不是为了记录这个事件而去经历它。 、年张立明开始收集整理哈尔滨这个城市内的声音,年哈尔滨声音地图正式与百度地图合作上线。在哈尔滨地图上有几十个红色的播放箭头,每一个代表的便是地图上那个位置存在于某个时间的声音。而那某个位置与时间,似乎组成了城市的一个立体架构,却也是立明老师无意为之。他行走于哈尔滨这个城市里,搜集了大量的声音信息,却又秉承了一股万事万物凭天然的劲儿,如他所说,“是你因为经历了这个事件而去记录它,而不是为了记录它而去经历这个事件。”在这整个项目中,他并未对时间与地点做刻意的要求。 张立明并非哈尔滨本地人,来到这个城市本身具备“客人”身份。本地人往往陷入自己的生活中,因为习惯使然,便无意识地将城市等同为自己的日常生活,跳脱不开,认为一切的出现理所当然。从而忘记观察,忘记思考。“客人”身份恰巧给张立明带来了对哈尔滨这个城市的新鲜感与热情及对这个城市的声音的敏感。而既然这热情是由“客人”身份带来,那么当创作者本人开始融入这个城市,这份敏感是否也会随着“客人”的身份消失呢? 张立明穿梭于哈尔滨城市的大街小巷录制了种种声音,风吹雨点拍打旗杆的声音、人说话的口音、小巷里的邻里交谈、地下通道的叫卖声,这些无疑可以呈现这个城市的一个个侧面。Hitlike将这些侧面整理起来,形成了声音地图。这些侧面是这个城市,也是你我所见的日常,那些存在着却被忽视的声音重新被整理出来以地图的模式呈现出来,有了他们在城市里一个位置。而那些再也不会出现的声音也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留存,当你听到那个时候的声音,再走到同样的地方留神细听,似乎城市的变迁也在眼前。 然而声音地图似乎还留有一些遗憾,它的出发点似乎全来自于一个带有“客人”身份的人面对一个新城市和对声音记录行为的热情,但整个项目没有发展成为一个可供更多人操作的模式,没有扩展为多城市,跨地域的模式。而这些声音在多大程度上能呈现哈尔滨这个城市呢?这也可以说是张立明声音地图的“哈尔滨”,可如果是这样这些几乎未经处理的声音个人化色彩似乎又太少了。声音地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档案性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化的? 然而,张立明老师接下来要操作的项目还是令人期待的——对声音的重新整理与调变,对声音的抽象性的理解。或许在此领域,他与声音会有更特别的相处。 栏目编辑:丛妙 相关网站推荐: 哈尔滨声音地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erbingzx.com/habyw/6854.html
- 上一篇文章: 又一山东籍女性官员重用为省委常委副省长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