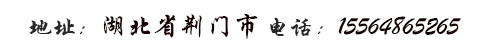哈尔滨开埠前的社会风尚
|
对于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说法。20世纪80年代,关成和先生提出金史上的“阿勒锦”即今天哈尔滨在金代女真语中的古称,含有“光荣和荣誉”之意,由此认为哈尔滨从年算起至年己有八百八十八年的历史}z}}-}.}3}3.m}。此后,关于哈尔滨名称的由来,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纪凤辉的“扁岛说”、王禹浪的“天鹅说”,均引起不小争呜,并都有专著发表。但是笔者认为上述说法均需要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进一步印证,目前,仍难以形成定论。 乾隆五十三年(年),哈市顾乡屯一带己有满、汉农民移居。随着“京旗移垦”和封禁政策的解除,现哈市平房、南岗、顾乡己建立更多的旗民屯落。其实,在此之前,关内北方诸省的贫苦农民在天灾人祸的逼迫下,为求生存,己千方百计地冒死“闯关东”。他们披荆斩棘,翻山越岭,沿途历尽艰辛,“凡转徙山林者,随处因树而屋,夜或野处熟火自卫,往往膏虎狼之吻,坠严谷丧生”。汉族移民的大量拥入,使一些地方出现“民户多于旗户”的局面,《鸡林旧闻录》又载“吉林省之土著,除八旗外,大抵山东人居多,百年以来,清廷政令解弛,佣工或挖参者先后纷集,日增月盛。凡劳力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其来时,肩负行囊,手持一棒,用以过岭作杖,且资捍卫,故称之为‘山东棒子”’。 关成和先生在《哈尔滨考》一书中详细考证出19世纪末哈尔滨周边“总共至少不下百村”地方史学者李述笑先生在其《中东铁路修筑之前哈尔滨是萧瑟寒村吗?》一文中也指出年中东铁路修筑前,“哈尔滨可以说是村村相望星罗棋布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19世纪末期的行政区划中,哈尔滨地区处于吉林和黑龙江将军辖区的接壤地带,并没有地方行政机构进行有效管理。在19世纪中叶以前,东北地区还保持着“龙兴禁地”的称号,从当时的政治文化角度考量,客观地讲,哈尔滨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化圈,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蛮荒状态。有鉴于此,正史缺乏对哈尔滨的系统记载就不足为奇了,但是从有限的方志资料中我们仍然可以对当时哈尔滨的风俗有一个梗概了解。 《呼兰府志》对当地民风有如下记载:“其时地方安谧,夜不闭户,牛马牧放于野,旬月不收,亦不遗失。乡俗敬官长,重气谊,无乾猴失德之事。官长及绅铃过其家,或投宿,咸款接,予以值不受。异籍之人饥驱北来,仓促无谋生策,借宿其家,无论素识与否,咸肯留养,期年数月无吝色”。 在饮食方面,“满洲宴客,旧尚手把肉或全羊。近日沾染汉习,亦盛设肴撰。然及款式不及内地,味亦迥别,疤人之艺不精也。所谓手把肉,持刀自割而食也。故土人割肉不得法,有‘屯老二’之诮。又云:“宴客无厚味,视家所有以烧猪为上敬。婚礼宴客,殷富之家,碗与碟数各十六,谓之四套,贫户八碗八碟谓之八八席”。 就穿着而言,《双城县志·礼俗志》载:“农工劳动者流,无论何时大多蓝布短衣,夏戴笠赤足。冬戴白毡帽,足着乌拉。’,《宾县县志·风俗略》载:“服装略分三种,曰衣曰冠曰履。男子无论满汉,春秋着夹衣,夏则大衫,冬则大棉袍外加马褂。色尚青,蓝次之,灰又次之。衣裘者二十之一。冠,夏草帽,春秋以毡,冬以皮。农工劳动者四季皆着短衣,妇女亦无满汉之分,袖短而微宽。其官绅多戴帽头……履则布呢皮三种,农人则着轨黝。” 就居住风俗而言,“家人妇子同处一室,老者之席距火洞近,次为稚幼,以火炕热度增减之差,为敬爱之别”。另外,边地苦寒,不论是土著居民,还是外来移民多嗜酒,“每三五成群,酣饮市肆,一日未终,罄其所有而后己,不知积蓄以贻家也。醉则随路倒卧,亦无人过问之”。 综上所述,直到十九世纪末期,哈尔滨地区的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区域地理上十分封闭;淳朴敦厚,豪爽好客对于民族性格风习而言是一件好事,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商品经济不发达,缺少重商言利的精明;从饮食、穿着、居住习俗可以看出当时哈尔滨开发的迟滞性与文化的落后性,甚至达到“问土人以富,数地以对”的情形。 (作者简介: 黄彦震,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系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东北区域经济; 胡珀,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哈尔滨市档案局主任科员,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东北地方史。 文章节选自《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年6月第30卷第3期《哈尔滨开埠前后社会风尚的变迁》) 整理:彭静 声明: 本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erbingzx.com/habls/9506.html
- 上一篇文章: 和祺服务哈尔滨企业家专场回顾不
- 下一篇文章: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宾县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