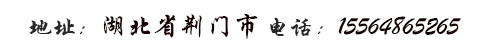哈尔滨的前世今生黄金年代与肮脏衰败
|
「豆瓣读书,让好书遇见你」 豆瓣用户 完颜穆尔登格/文丨本文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允许,禁止转载丨 20世纪初中国有过两个东方巴黎,一个众所周知是日益繁华的上海,另一个是已经衰败的哈尔滨。 那时的哈尔滨是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各类欧洲流亡者的第二家园。由于清朝长期封闭白山黑水,关外一直人口稀少,直到《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让大片土地后才,清政府开始重视有效行政控制。然而日渐衰落的清朝事实上已无力顾及关外。远东地区成了俄国与日本的角力场。以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为契机,形成了新枢纽城市哈尔滨。大量俄罗斯人,波兰裔铁路工程师,各国商人纷纷迁入,他们不分国籍种族,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哈尔滨人”,这才有了哈尔滨最好的时代。 相对于当时的寒冷、贫穷、苦难,“哈尔滨人”更喜欢在回忆中给自己的最初的“故乡”染上温情与浪漫的色彩。有一篇专题文章《波兰“哈尔滨人”忆抗战:在那里我们共同经历好与坏的年代》曾记录了很多“哈尔滨人”对旧时代的回忆。 ——年出生的波兰人奥耶维奇,父母于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相识,战争年代结婚。他回忆说,那个年代的哈尔滨是一座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共存的国际大都市。“当时有很多俄罗斯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美国人等。父母经常对我说,虽然当时有很多国家的人居住,但是之间并没有民族冲突。大家都互相尊重,还参加对方的节日庆祝活动。二十世纪20年代是哈尔滨发展的黄金年代,那时人们的生活很好。”但是,奥耶维奇接着说道:“93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最怀念哈尔滨时代的大概还是设计建设了这座城市的俄国人,这座城市承载了他们在远东的美好的梦,这个梦却因二战而破碎。有一部俄剧叫做《一切始于哈尔滨》,讲述了一对俄罗斯青年的爱情故事,记录了20年代哈尔滨俱乐部中风行的靡靡之音。男主角正是中东铁路的工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接管铁路,压迫铁路工人,更对哈尔滨外国“原住民”实行了严密监控。 国内现在常常喜欢提到二战期间日军在满洲搞的基础建设都被苏联红军掠夺走了,结果从另一个视角来看,更早的时候,“哈尔滨人”本来就在有条不紊地建设包括远东铁路在内的各项基础建设,却被二战打断了,被日本人抢走了成果。 ВсёначалосьвХарбине里的中东铁路工人在战前的黄金年代里,在哈尔滨经商大概是件挺时髦的事儿。在俄罗斯时,玛格丽特奶奶给我看她保存的黑白照片和一个世纪前亲戚从哈尔滨寄来的明信片,这位亲戚在哈尔滨的制药公司工作,还有一位中国妻子。 到底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各族裔各阶层的人的记忆当然不一样吧。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哈尔滨有过于美化的记忆。有一部《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依我看来更客观。 这是一位德国犹太小提琴家的回忆录,20世纪30年代末,斯特恩一家人为躲避纳粹迫害辗转逃到中国哈尔滨。除了以9岁才开始(对于小提琴家来说这个起步实在是太晚了)在颠沛流离中学琴还能进入以色列及柏林爱乐乐团这不可复制的奇迹外,他对于三个不同年代的哈尔滨白描也十分精彩。他这样写道: “哈尔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她作为经过西伯利亚过境火车的枢纽出现于9世纪末叶。那条铁路横穿整个大陆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条支线从黑龙江的边界城市满洲里向南一直通到旅顺港。年以前旅顺港在俄国人手里,日俄战争中落入日本人之手。 起初,哈尔滨只是满人部落的一个屯据点,但是发展很迅速。俄国的铁路铺到那里,所以那里的房子大都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哈尔滨有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许多中国人从南方蜂拥而至,从山东省来得特别多。他们成了这里的铁路工人,在那里干最沉重的工作。于是出现了一个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区,相反,俄国人和欧洲人则聚居在松花江边的市区,两个区很快连在一起成为一座大城市。俄国流亡者建立起的漂亮的大教堂给这个城市打下自己的印记。” ВсёначалосьвХарбине里的中国人这些穷困的外国音乐家常常要在饭店、婚礼等场所演奏助兴,冬天哈尔滨是那么寒冷,迎亲路上琴弦常常断裂,这正是书名的来源。二战末期,日军越发丧心病狂,对任何潜在的奸细都更加警觉,每个外国人居住的院落都新搬进一家日本人,以监视他们。可是战后以音乐为生的“哈尔滨人”的处境却越发糟糕,原有的乐团解散,饭店与咖啡厅成了变相的妓院,音乐家丧失了音乐家的尊严。接替日军的苏联红军军纪之差已是众所周知的,“哈尔滨人”在严寒与贫穷之上,又多了性命之忧。所有人都想逃离哈尔滨。经过数不尽的苦难后,斯特恩一家终于逃离哈尔滨,到了以色列。 后来的哈尔滨变得很好吗?在我们的印象中,它随着整个东北,与曾经的国有工业体制一起衰败下去。在斯特恩的回忆录中,也印证了同样的印象。年,随柏林爱乐乐团方华的斯特恩重新回到童年生活过的哈尔滨,而这里却是这样一幅景象: “哈尔滨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城市,它只是一个灰色的大工业城市。我觉得它就像我在时一样封闭。那里的文化生活,我所能经历过的那一部分,和流亡者一起消失了。从事艺术的许多中国人离开了哈尔滨,现在生活在北京或是上海那样的开放城市里。” 文化生活的消亡又能怪谁呢,在某些众所周知的经济布局以及政治运动原因下,曾经的活力都已经被扼杀。 “这个城市,首先是空气很肮脏。尽管这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城市,但对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投资。取暖主要用质量很低劣的煤。那些老房子,甚至俄国人盖的青年风格的美丽房子,也从来没有维修过,新盖的四五层以上的难看的楼房几年以后也就变得不堪入目。文化大革命的暴徒把俄国的教堂,早先城市风貌的主导建筑拆的只剩下一个。甚至连中央大教堂,那个坐落在市中心山头上的大教堂也被夷为平地。” 中国特色的拆哪甚至毁掉了很自己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又何况这种外来文明的都市呢。而当年选择留在哈尔滨的外国老人的境况也十分凄惨,住在破败的房屋里,继续忍受每年持续半年的寒冬,靠中国政府一点微不足道的养老金苟活着。 整个东北几乎与中国近三十年的飞速发展无缘,哈尔滨的衰败只不过是东北衰败交响篇章中的一个声音。年斯特恩再次看到哈尔滨的样子: “哈尔滨让我非常失望。这个城市在我们年到达时人口在50万到万之间,今天那里有万人口,还在不断增加。高楼大厦林立,看起来,与香港、东京或者曼谷没什么两样。大楼旁就是丑陋的住宅,但也有大商店和旅馆,这一切与我们认识的老哈尔滨没有一点关系了。经济上的巨变也带来了社会的变化,贫富同时产生。在这里,对于文化领域来说,楼房越高,用于文化的钱越少。(除非把迪斯科舞厅,卡拉OK和运动场都包括到文化的概念里。)” 尽管现在旅游部门把哈尔滨宣传成美丽的冰城,这里的肮脏与衰败却是无法掩盖的事实。 去年在布拉格我见到一个在哈尔滨留学过的斯洛伐克人,他用他有限的英语与我交谈。我问他“喜欢在哈尔滨的生活吗?”“不喜欢。”“为什么?”“那里非常冷,而且非常脏。城市一点都不美。” 那个有文化魅力的,有包容性的美丽国际大都市只存在于国际流亡者,老“哈尔滨人”的回忆与传说中。(以及我们的自欺欺人中) 参考: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aerbingzx.com/habtc/7581.html
- 上一篇文章: 哈尔滨还有这些好玩的地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